(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7辑)

19世纪肇始于法国的象征主义诗学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学思潮。自20世纪上半叶起,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对中国诗歌的影响经历了接触、融合、转化的系列过程,成为中国诗歌从古典转向现代的重要世界文化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当代多民族诗歌创作进人空前繁荣期,以阿库乌雾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人迅速成长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股新生力量。从处女作《走出巫界》到21世纪新作《混血时代》《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汉英对照)》,再到当下仍持续进行的微博写作,阿库乌雾在不断深入彝族民族历史文化的同时,试图通过诗性思维触摸人性深底和人类共通的命运,在实践自身美学追求和人生追求的同时淬炼出独具一格的诗体风格。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当代诗人在新语境中对法国传统象征主义诗学的重构过程。当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遭遇的主体由单一民族背景作家变为多民族背景作家之后,作家身后的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多重叠加使其接受结果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同时,全球化语境对中国本土诗歌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多民族诗歌创作逐渐需要具备一种全球性的品质,且要被纳人全球审美视野和审美标准下进行考量,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诗歌思潮洗礼后的本土写作”。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重构正是基于这两点展开的。

“洞观者”(visionnaire)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对诗人在诗体语言中的身份的一种基本定位,它改变了以往诗人的叙述视角,将诗人从“观察者” (observateur)的身份中剥离出来,通过外位性凝视使诗体语言的叙述呈现出客观冷静的风格。这一观念源于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契合论”。波德莱尔认为,诗人创造的形式和语言是神秘的另一世界,这个世界与自然有着某种神秘的响应,即契合、感应的关系,自然本身具有“形式、姿态、运动”“光和色”“声音与和谐”三种形态,这些形态总是呈现在面前,总像谜一样包裹着我们,因此理想的诗人应该数学般准确地翻译自然,但又隐晦地表达出晦涩的、被朦胧显露出来的东西。“契合论”传达了一种美学观念,即“诗不是再造自然,而是创造与自然具有‘契合’关系的超自然的理想世界”。在这种诗与自然的关系中,诗人就应该是能透过幻象看见事物本质的“洞观者”,是能够“通过诗来表达生命的神秘的人”。后来兰波(Arthur Rimbaud)的“我即他者”和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诗人无自身面目”都是对这种作者外位性观点的继承和延伸。阿库乌雾曾称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是对自己影响最为深远的西方诗学流派,他的诗体书写在表现诗、自然、人的关系时确实契合了“洞观者”的诗学观。在《碎片》一诗中,阿库乌雾通过外位视角将“云雾”“星星”“泥土”“江河”都隐喻为“碎片”,使其成为诗人洞观世界本相的载体,继而通过通感让“云雾”与“轻盈”、“星星”与“浩翰”、“泥土”与“生命”、“江河”与“血脉”形成相互感应的关系,在美学上营造出非现实的艺术世界与现实的自然世界之间某种意义上的应和关系,最后以客观凝视揭示出“碎片是世界的本相,世界若有本相”的对应关系。在《边缘》一诗中,“河流”“大地”“彼岸”“此岸”“森林”“海洋”都作为人的外在事物和对应物出现,就连“那个享受过特殊孤独的种族”也是外位性的,它们与诗人之间也建立起一种契合关系,诗人通过与浪漫主义直抒胸臆迥然不同的语言形式将自身隐藏,使主观凝视消弭,视野所及均是他者凝视,如此“截不断”“托起”“吞噬”“重建”都成为“洞观者”外位视角中人与事物的动态表征。在这一点上,阿库乌雾与波德莱尔是一致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主义流派诗人只关注诗人在语言世界中的虚构身份,他们所追求的他者视野是完全脱离诗人主体的客观存在,而阿库乌雾构建的“洞观者”却表现出诗人在现实世界和语言虚构世界中身份的关联,凸显出二者的共构关系。也就是说,阿库乌雾笔下的“洞观者”虽然具有他者的外位视野,但思维却糅杂了诗人现实身份中的主观精神,因此他笔下的他者凝视并不完全是脱离诗人主体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外位视野中不时闪现诗人主观精神的光辉。这种二元共构性之所以能够在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中得以实践,根源于诗人现实身份的多元遭际。阿库乌雾出生、成长于大凉山深处的彝族地区,成年后赴成都进人西南民族大学接受现代化教育。他的诗句“从‘ap kup vyt vy’到‘阿库乌雾’再到‘罗庆春’,我的姓名链环锈迹斑斑”正是诗人由单一民族背景变为多民族背景后身份变化的写照。诗人遭遇汉语之后的生命历程从“第一母语”的彝语世界进人“第二母语”的汉语世界。姓名变化的背后是新旧身份的叠加。诗人在潜意识里不断返回“ap kup vyt vy”,但又不断对“罗庆春”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获取源源不绝的创作激情。“ap kup vyt vy”和“罗庆春”是诗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两重身份,二者相互重叠,成为其深度接受彝汉文化智慧、体验双语遭遇、实现双语人生的前提。这种遭遇正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新时期的特殊体验,即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的文化、语言、身份之间的屏障被打破,“文化混血”成为历史必然。在语言世界中,现实身份化为思维,凝为文字,表达着诗人观察世界、审视世界的态度和方式。“ap kup vyt vy”使诗人在审视自然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联想本民族的生活环境,发挥彝人的神性思维,展现彝人的精神内核。有的诗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毕摩文化气息,《碎片》中的描述带有明显的神性思维,《边缘》中 “旷古的森林”让人不禁联想到大凉山深处的广袤林地。同时,阿库乌雾又不断尝试冲破藩篱,“罗庆春”的身份使诗人获得了与包括汉语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接触、交流的机会,从而获得了在视角上无限延展的可能性。法国传统象征主义诗学中的“洞观者”与诗人现实身份的关系是对立的,“我即他者”是将自身泯灭,以他者取代自身而去追求绝对的客观,而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则撕裂了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在他笔下,外位视角背后的“洞观者”是有着诗人血肉的躯体,诗人在语言中只是将躯体隐藏,但其精神仍然存留于视野之中。由此,他所塑造的他者凝视自然聚焦“混血时代”中人与自然、民族与自然的关系,《边缘》中“那个享受过特殊孤独的种族”展现的正是诗人在双语遭遇的深度焦虑、深度尴尬、深度旷达、深度通脱中对本民族的回望。
云雾是碎片,启迪了轻盈的含义;星星是碎片,告白了宇宙的浩瀚;泥土是碎片,孕育了生命的花朵;江河是碎片,警策人类危机来自血脉。碎片是我们的本质?碎片是我们的优势?碎片是我们聚散自如的机制和结构?碎片是世界的本相,世界若有本相。
河流截不断大地,彼岸与此岸同时呈现,彼岸与此岸从来就互为边缘。于是,黄昏的叶片再次托起古朴旷世的森林,边缘就在黎明的枝头。而黎明的花朵吞噬怒潮狂涛的海洋,边缘在岩石的底部,在那个享受过特殊孤独的种族深处。
鸟巢被毒蛇占据你们重筑鸟巢!
狼窝被玉兔拥有你们重建狼窝!
边缘,送葬的人群
走在正午的阳光下!
——《边缘》

自波德莱尔起,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美学主体——“恶之美”。“恶之美”崇尚诗的自主性,认为诗“不以真实为对象,只以自身为目的”,不应将善和美混淆,诗的目的就是在恶中发现美,这种与现实主义所秉持的功利艺术主张截然相反的观念构成了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美学基础。“恶之美”这个美学主体自诞生之初就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塑造的城市有着“阴郁的情爱、有罪的喜悦”,“黑夜建立了王国,势不可当,黑暗、潮湿、阴森,令人不寒而栗”,这样的城市意象是以19世纪的工业重镇巴黎为背景的,掩映着西方工业革命时代诗人在社会变迁和城市发展中的无限彷徨和深沉思考。
时代变迁、地域转换,伴随着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在全球的传播,“恶之美”在新境遇中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从早期“大红公鸡的鲜血/裹挟着朝花似的咒辞”,到《性变》中勾勒的后现代的“病史”,再到《混血时代》中的“罂果”“粪便”,其所塑造的意象与波德莱尔诗歌中恶的意象遥相呼应。但诗人的主体遭际对其美学建构的影响也将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与传统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区别开来,主要体现为两点。
其一是诗人的个体境遇对“恶之美”内容的丰富。在现代文明侵人大凉山神秘的彝族社会之前,毕摩文化主导下的彝人对世界早已有了自己的想象和表达。动物、植物、可见和不可见的神秘生物,以及各种超自然力量,都出现在彝人的想象空间里,呈现于世代相传的口述文学或独特的文字记载之中。阿库乌雾是在继承这些民族的传统想象和表述的基础上,将典型的法国象征主义美学主体融人自己的诗体书写之中的。《混血时代》中那些叫“硕诺笃基”的毒草,彝人传说里的“鬼蝶”。这些意象都沾染着彝人的民族文化气息,成为勾连彝人神秘世界和现代世俗世界的媒介。由于阿库乌雾个体境遇的特殊性,“恶之美”在其笔下被赋予了彝人的民族文化因素,成为该美学主体在域外接受过程中实践民族转向、本土转向的一种显性表征。
其二是诗人的社会境遇赋予“恶之美”的新内容。阿库乌雾所处的社会境遇在地缘和发展状态上都曾发生突变。他在采访中曾称自己有两个家园,一个是18岁之前居住的位于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金沙江流域的一个彝汉杂居的山寨,那里今天依然保留着典型的山地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生态;一个是读大学以后长期居住的现代化大都市成都。社会境遇的突变改变了诗人的创作视野,使其能够挣脱单一民族文化的局限而去深层思考当代社会、民族、文化、人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恶之美”又成为阿库乌雾观照其社会境遇的美学主体。城市生活启发和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互动,城市的喧闹与孤寂,城市的欲望与贫乏,为诗人的创作注人了无形的张力,开拓出特殊的心理空间和精神境界。在诗人笔下,城市成了一座现代技术装备的森林,也是一头怪兽,而人想要在城市这个丛林里保持某种本有的自然属性是十分艰难的。“城市的掌心早已成为鼠辈的巢穴”,阿库乌雾对城市的描绘一方面沿袭了波德莱尔式的阴郁和冷静,另一方面这些“恶”意象所代表的是阿库乌雾面对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技术等种种冲突时的彷徨与深思。阿库乌雾塑造的无数个“恶”意象无一不在践行这一目标:“可以变灰指甲的指甲,在城市的纹路里成为时尚”“广告牌土壤一样生长,并有止血的功能”。每一个意象都映射着诗人周遭的现实,由此,这些恶的主体也摆脱了固有模式和陈词滥调,在独属于阿库乌雾的诗歌语言系统中熔铸成形。阿库乌雾的社会境遇使“恶之美”这一美学主体在域外接受过程中实现民族转向、本土转向的同时,也将诗人对人类社会演进、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纳人其中,从而突破思维的时空桎梏,使其现代性构建步人新的阶段。
城市是传说中的怪兽么?城市里兽与兽的故事从未停止;城市是史诗里的天堂么?可城市里的神仙吃尽人间五谷杂粮;城市是大地上长出来的蘑菇的变体么?犹如我的身体上长满鲜嫩的肉蕾;城市是遗留在梦中的古战场么?据说梦中的战乱比现实中的战争还激烈;城市是人兽共享的欢乐宫么?宫中的欢乐让城墙长出裂缝;城市是人类永恒迁徙途中暂时的驿站么?脚印像花草一样枯荣;我带着迷惑的箭镞继续守护着身边这虚虚实实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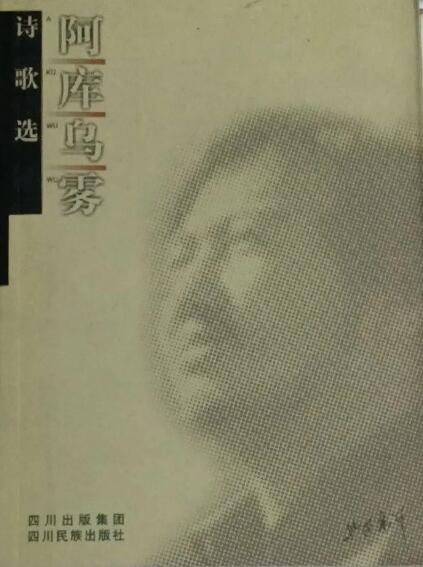
与许多早期在法国接受过象征主义诗学直接熏陶的中国诗人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阿库乌雾从未去过法国,不懂法语,更未从事过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工作,他是地地道道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诗人。他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习得和对这一流派诗歌作品的品鉴一方面来自中国作家、翻译家的译介,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早前直接在法国接受过象征主义诗学影响的中国诗人的作品的影响。这两种途径意味着,在当今,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人了本土化时代,即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不是直接生成的,而是间接甚至多重间接生成的。这种间接生成的过程使阿库乌雾在接受中表现出更多的本土化属性。
一方面,这种本土化属性源自彝文化与汉文化、彝语与汉语的共构。我们在品评阿库乌雾诗体书写的表述视角、美学追求时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所有这些表征最终都将落实于语言本身。在语言上,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可以分为两大板块:彝语诗和汉语诗,汉语诗占多数;从他还在持续的创作的趋势来看,汉语诗还会更多。这和阿库乌雾的语言观,进而和受语言观影响的诗学观,都是密不可分的。早在20世纪末,阿库乌雾就曾提出“第二母语”和“第二汉语”的观念,即在原有单一母语文学传统被颠覆的时代,中国少数民族诗人开始用汉语写作,在自觉回溯本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同时,实践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汉语成为“第二母语”。这些先天带有人文差异的作家在创作中又不断对汉语的表述形式进行创新,他们“通过自身的人生体验和感受,有意识地改变汉语使用的各种逻辑..不断地突破单一民族语言及其文化界限,让自己对母族、对历史、对命运的真实感悟借助汉语这种有力的工具来实现少数民族作家在双重文化熏陶下的个性展示”。汉语已不再是原有汉文化意义上的汉语,而变成了经过多民族作家全面变构的新的汉语,“第二汉语”成为现实。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中读到如此多的用汉语表述并承载彝人文化精神的诗句。
另一方面,这种本土化属性也来自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当今时代的本土境遇。相比于一般作家,少数民族作家会面临更多的危机,如母语生存问题、外来文化压力问题等。阿库乌雾曾提出,要实现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健康发展,少数民族作家“必须以自觉体悟颠覆母语文学传统,甚至颠覆母语文化传统的精神失落感为前提,在更高也更深的层面上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母语’元叙述‘方式加以全面背叛”。这个过程必然会产生许多的痛苦和彷徨,这些情感自然反映到作品中,所以我们经常能在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中看到富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关于母语、族群、文化的讨论。同时,在消费经济、互联网和多媒体飞速发展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作家也要面临传统写作所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在不断调试的过程中,创作方式和诗体语言最终的呈现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本土境遇中阿库乌雾所遭遇的危机、痛苦、彷徨也都融于他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接受之中,最终形成独属于他的诗体风格。
由此可见,在以阿库乌雾为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诗人身上,这种本土化属性本身具有异质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接受也自然糅杂着异质的、多样的、复杂的特征。彝文化与汉文化、彝语与汉语的共构,诗人的本土境遇,都使阿库乌雾诗体书写的“洞观者”凝视和美学构建呈现出区别于法国传统象征主义诗歌的特色。
同时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又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开展的,全球性是阿库乌雾实践世界文学思潮洗礼后的本土创作的前提,也赋予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以世界化属性。世界化属性拓宽了诗人的视野,让诗人既能冲破民族藩篱去关怀人类的终极性意义和本体性层面,又能以诗性照耀,从异域回望本土、回望母族,世界文化、世界问题成为诗人创作的一大源泉,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像《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汉英对照)》这样的民族志旅美诗歌集,正如美国诗人本德尔(Mark Bender)所描述的那样,“他(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受到一连串事情的激发,从俄亥俄州他临时的家门前盛开的花,到太平洋的波涛。有时他的诗歌又关注北美最古老的文化,今天,这些400多个部落的土著人遍布这片土地”。世界化属性不仅拓展了诗人的创作主题,也丰富了诗人的语言形式。在阿库乌雾的语言观中,“第二汉语”的概念本身包含了汉语从外国文学、外国语言中借鉴而来的一切文学艺术表现手法的汉语化过程。因此,在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中,不仅有“明尼苏达”这样的汉语音译词出现,也有“Four sisters”“NEIL”“Fours Colors”等英文词的直接植入,由此阿库乌雾诗体书写的语言载体有了诗体世界语的属性。通过阿库乌雾独特的世界视野和诗体语言,法国传统象征主义诗学中的诗人身份和美学主体也有了世界化属性和人类终极关怀。

阿库乌雾在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重构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诗体书写形式,这受益于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不断追求,即发现、发掘世界文化、文学中的新鲜养分,这也是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能够长盛不衰又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源。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多民族、多语种、多美学传统和多种信仰背景的文学史,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多民族诗体创作必然受到世界文学思潮、美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在文化、文学”混血,的新时代,法国象征主义诗学融人阿库乌雾的本土精神和艺术手法之中,成为其实现从”走向世界,到”走向自我,,达到用母语与世界对话的诗学理想的重要因素。阿库乌雾诗体书写的特征不囿于普通意义上的作家个人风格,它既体现诗人的个人精神追求、美学追求、创作追求,又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语言特征密切联系,其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重构所彰显的正是当今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中国多民族诗歌参与中国文学全面转型和自觉构型的历史使命。尽管阿库乌雾的诗体书写留有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痕迹,但阿库乌雾不属于任何主义,阿库乌雾就是阿库乌雾。
(本文作者:唐桂馨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
-- END --
中华美网编辑/匡德胜

 中华美网首页
中华美网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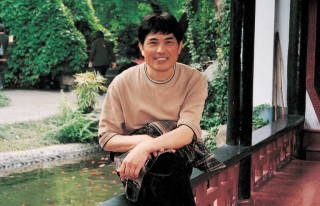








提交